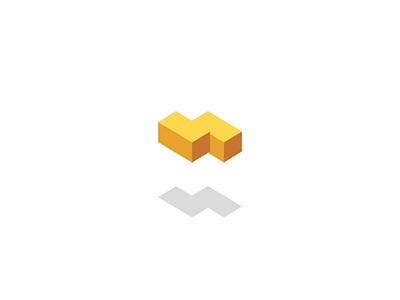中国有没有宗教?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中国宗教?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一是基于涂尔干社会学观察和理解下的范式预设,即宗教观念与宗教仪式的二元论理论框架以及由信仰表达和仪式生产,象征社会的集体表象。简单的说,西方的宗教,特指基督宗教有明显的特征可供观察,体现在制度性、组织性、社团性···,有系统的,逻辑的教义言说和承传的,象征的仪式表达。二是在religion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产生之前,religion这个词主要指的就是基督宗教。后来到了17、18世纪,基督教面临异文化的挑战后,逐渐认为所有相应的民族和文化都有宗教,所以religion就演化成religions。今天,我们看到的、学到的 religion这个词是基督教遭遇异文化,经历了自我反省后包容了所有人类文明中的宗教而进行调试后产生的一个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词汇,不能再把它等同于基督宗教去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将“religion”这个词翻译成宗教。所以现代汉语里的“宗教”一词来自于日语外来语,而非从古汉语中而来,也就说这个词是借来的。否则我们找不到哪一个中国古代词汇去对应现代意义的religion一词。总结这两点,简单地说,一是中国是否缺少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集体表象?二是中国古汉语词汇里没有“宗教”一词。那么,我们该质疑中国有无宗教?
在彭牧博士的《Religion与宗教:分析范畴与本土概念》一文中,文章作者引用陈熙远的话说,“实际上构成‘宗教’的这两个汉字各自都有丰富的历史,而且合成词‘宗教’也非在现代才出现。“宗教”一词在六世纪的佛经中就已经出现了。religion的前现代意义是与佛教相关。中国学者借用了日语词汇“宗教”一词后,它才被赋予了新的,更加宽广的意义,脱离了前现代单指称佛教的狭窄意义。 陈熙远还认为,在20世纪,中国学者其实并没有把它当借词来看,而是依照中文构词法去理解和使用,即从两个拆分的汉字,“宗”和“教”去理解。获得新的意义后,这两个词便彼此融合,不再分开。
“宗”在词源上看,有祖先的含义,祖先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宗”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与人之间的血肉关系而非不着边际的人神关系。它的宗教性唯独在于对祖先的敬重,相信其死后依然存在。基督徒要经历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但祖先崇拜不然,这是明显的事实,不存在信还是不信。中国人每年的祭祖和扫墓,都要在祖先的墓碑前献花、鞠躬,甚至对祖先说话。如果祖先生前抽烟,还要为其点烟。佛教虽然也是外来宗教,但文中说,魏晋以后,佛教借用了“宗”这个祭祀有血缘关系的灵魂这一意义,发展出了支派的概念,如天台宗、华严宗···就好像属于某某家族,某某同族。再一个,佛教模拟了亲属称谓,在僧侣之间构成了虚拟的家族关系。文中说,从五世纪起,所有中国和尚跟着释迦牟尼姓,都姓释。起名方式遵循世俗的原则,同代和尚第一个字相同,由此在僧侣中模拟构建了兄弟关系。 对“宗”这个字内在含义的延展发挥是中国历史上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进行中国化的一次成功试验。
而“教”字从中文原义上看,有“教化”的意思。不管它是作为动词义还是名词义,“教”强调的都是上古圣人的教诲实践或言传身教的方法。也就是说“教”强调的是人。如谁教的,教的方法是什么。与西方人理解的“教”不同。在西方人看来,“教”指的是一套实体、一套体系。中国人认为“教”的源头对“教”的对象产生效果和影响,以达到“化”的目的而非教义体系自己产生某种效果。正因中国人把它理解为人的一套说教,而且“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并不太关注说教中的正教与邪教、正道与邪道之分,中国历史上才很少有西方教派之争。
并且,中国人的宗教实践不像西方社会,它与社会文化中的其它领域明显缺乏界限。正如杨庆堃的观察,宗教弥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难以清晰辩识。 但从中国人祭祀祖先灵魂的古老传统以及成功走上中国化道路的佛教来看,不能说中国没有宗教。在中国广褒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 只是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集体表象相对模糊和分散。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也逐渐有了组织性、制度性,但与佛教进入中国相比,尤其是与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的佛教相比,相差了近十三个世纪。而且在祭祖的问题上,尤其是明末清初爆发的“礼仪之争”更使得上至朝廷,下至士大夫、老百姓对基督教产生抵制和作难。而且基督教自己有一套正统的教义学说,它不会如中国人的理解,哪怕是与正道相对的歪道、左道也被接纳为道或教的一部分。假如中国宗教必须符合“宗”和“教”两个拆分的汉子分别在词源学上的含义或者必须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延伸义,那么基督教能不能被纳入如祭祀祖先,佛、道等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的宗教格局中去?这个问题要带着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历史上,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第三次在明末清初,基督教采取了很多适应本土的策略,后来因为祭祖的问题、中国禁教而以失败告终。第四次是最不光彩的,因为基督教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伴随着列强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至今还存在基督教是“洋教”或者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等不光彩的声音。为了使基督教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而不是基督教在中国,20世纪初,中国教会发起了自立运动,到今天一直在推进的基督教中国化,说明中国基督教还在路上。与佛教的中国化程度相比,虽然距离还相差很远。但至少基督教在努力调试自我,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比如,中国的基督教堂上挂着一个大大的 “爱”字。爱在基督教的文化语境里有圣爱(神对人无私的爱)的意思,在儒家文化里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就是“仁爱”,就是利他的,超越自我中心的爱。 儒家忠君孝亲的伦理本就是要用爱来维系。在祭祖的问题上,基督徒虽不跪拜、烧香,但是却可以纪念和献花,慎终追远。而且基督徒更强调与活人的关系,即另外一个中华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还有,大部分的中国教堂,十字架都被涂成红色。在西方,很少看到十字架被涂成红色。一是可能让中国信徒联想到耶稣的血染红了十字架,二是因为中国人喜爱红色。红色代表吉祥,也有斗争、逐恶的含义。如在中国古代,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官吏的服饰多以红色为主。所谓“朱门”、“朱衣”等。耶稣为信徒带来了吉祥,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驱逐了邪恶。还有,之前笔者说佛教延伸了“宗”这个字的含义模拟了亲属关系,在僧侣间构成了虚拟的家族关系这点,其实在基督教里也能找到对亲属关系的模拟。在教内,所有的人相互称兄弟姐妹。源于耶稣受难前为门徒洗脚,如今成为教会一大传统的濯足礼,在复活节前的周四,非血缘关系的双方互相洗脚以效法耶稣爱人的榜样并强化这种爱的意识。包括基督徒探望受苦的人与那受苦的人一同流泪哀叹,正如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彼此洗脚,共同哀哭,互称兄弟姐妹正是一种对家族间人与人之间血亲关系的模拟和实践。只不过它在未遭遇中国文化之前就有了。只能说这是偶然的重叠而不是基督教遭遇异文化后努力做出的适应。以上列举的例子都是外在层面的,如组织上的、形式上的等。最难的则是思想层面的中国化。
从20世纪初到现在,先辈们下了许多功夫,但更多是在表象上的“化”。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做到表象上的“化”了。中国的教堂风格普遍是哥特式的,甚至有人认为教堂只有盖成哥特式才像教堂。基督教的诗歌虽然有些用中国传统曲调取代了原有的源自于西方的曲调,但大多数还是源自外国。神学院使用的教科书大部分还是翻译自西方学者的著作。即便是中国基督徒学者的著作,也多以介绍西方流派和学术观点为主,参考文献也基本是外语文献。
什么是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以草创时期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一位名叫海老名弹正的基督教思想家为例。他成为基督徒后毕生的目标便是使基督教日本化。就是让日本人觉得基督教其实与日本文化并不疏远。由于受到儒教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的影响。效忠君主、父子有亲的传统思想在海老名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自明治维新之后,海老名经历了一段君臣关系的真空时期,而正是基督教的上帝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为他找到了一位他可以永远侍奉的君主。海老名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出发,以已为臣,以上帝为君,以儒教教导的君臣关系来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在他经验上帝的过程中,体验到己为子,上帝为父的父子关系也十分明显。他认为,“在基督的意识里存在着与神在伦理上的父子有亲的关系”。 也就是说基督作为子在表达与父的关系上时将儒教的孝悌精神作为人的榜样确立下来。人类的至善、人性的光辉可以在基督的生命中得到完美的表达。上帝与基督存在如同五伦关系中父与子一样的伦理实质。但是他的这一番作为其失败的意义远大于成功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人,后来被神提携成为神。在本体论的理解上,他只是接受耶稣成为神的儿子而不接受耶稣在太初就与神同等。可以说,海老名在类比儒教与圣经真理的积极探索中寻找到了父与子、上帝与基督在伦理实质上相类似的表达,但是因拒绝承认基督与上帝同等,所以被定为异端。虽然被定为异端,但是他的贡献在于通过耶稣与上帝的关系模拟了儒家文化语境中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和忠孝伦理。臣子如何忠于君,儿子如何孝顺父亲,基督徒也要怎么样忠于上帝,孝敬上帝。但不同的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语境中子与父平等,而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子次于父,臣服于君。圣经中表面上耶稣顺服上帝,其实是立下一个前辈顺从的榜样。这让笔者觉得,思想层面的中国化在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在universal的层面与大共基督教神学传统产生分歧。cultural层面的和universal层面的界限在哪里?所以基督教还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基督教在中国(Church in China)向中国基督教(Chinese Church)努力。
综上所述,虽然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在某些方面吸收了一些中国元素,但是基督教自身决定的一整套教义系统决定了它无法完全符合词源学上“宗”和“教”原本的含义,有时也不得不与文化划清界线。超越性和它有限的包容性使得它在遭遇异质文化后一方面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筑造起藩篱和围墙。笔者想说,基督教之所以不可能完全并入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的宗教格局中去但是现实中又作为当代中国五大宗教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在拯世救民上与其它宗教所共有的速效法门和朴实直接的道德劝导这两大低级门槛。哪一个宗教能顾念众生之苦恼,使众生在成圣成佛之路上如水路乘船而非陆道步行,哪一个宗教就能昌盛。唐宋时代的宗教之所以兴旺发达,其原因就在于不仅上有作为精英阶层的僧尼、道士、儒生,也同时混合了处在社会底层的乡民群众。上至精英、下至百姓共同构成了一副生动活泼的中国宗教全家福。因为儒释道各有其低级别的准入门槛。对于佛教来说,僧俗都可以受菩萨戒;对于道教来说,道士可以在家并拥有婚姻生活;群众可以参与醮义,赶考的人可以礼拜文昌星。对于儒家来说,凡认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价值观,包括祭祖和守丧的就自然被囊括在儒教内。 对于基督教来说,内心虔诚的信仰,才是往生天国的前提条件。相反,对于诺斯替教、犹太教、摩门教,古希腊宗教等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如诺斯替教强调禁欲主义修行对于救赎的必要性,犹太教强调割礼和律法,摩门教强调清规戒律。 道教的《太平经》中也有类似道德规条对于成仙之必要性的说法。正如其中有一段话:“人无大功于天地,不能治理天地大病···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异有功之人也”。 也就是说,只有上天认可一个人的品行,这个人才可能成仙,品行不端的人在未得到上天允许的情况下,绝不可能获得成仙之道,也不可能登上天宫。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福音可以迅速在巴勒斯坦社会赢得大批群众。正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因为安息日的主竟然宣告人并不需要在字句中刻守安息日,而是应该藉着信心回应上帝的爱,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享受心灵上的安息。因此判断一个宗教是否融入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不仅在于强调宗教符号或神学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也应该从社会学的层面考察一个宗教何以能被普通大众快速接受和实践?而当一个宗教被广泛的获得社会认同时,是否中国化程序就被受惠者自觉启动,执行并寻求转化方案?
参考文献:
1.(美)杨庆堃(C. K. Yang)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何光沪著:《天人之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日)古屋安维等著:《日本神学史》,陆若水,刘国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4. 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宗教试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2016年。
5.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6.彭牧,“religion与宗教:分析范畴与本土概念”,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5期。
(注: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专业课程研修班学生)

本文原载于“信仰和学术”微信号,本平台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